译文及注释
译文
惠远祠前蜿蜒着古晋国的青溪,翠绿的萍叶和银白的浪花清澈见底,
水上的悬瓮山像是卧着的屏风,一派郁郁苍苍长达三百余里。
你这中原的北门气势多么雄壮,云烟笼罩着城阙还能让人想象,
山上的望川亭看够古今巨变,只留下春风吹起的阵阵麦浪!
那龙头般的系舟山被砍去龙角,白塔无端被毁,城池惨遭扫荡,
薛王已经投降,人民还在抵抗,屋瓦就是箭头,纷纷飞向敌方!
汾河水淹没了晋阳古城,太原府被迫迁到唐明村。
自从失去这道屏障的光彩,河洛一带便遭受外族的入侵!
想当年宫殿上雕着苍龙玉虎,高耸的金雀直上空中的云雾,
不论是民居,还是官府衙门,以及那百余座佛寺道庐,
花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,为什么一把火烧成焦土!
到如父老们仍旧对天哭诉,恨当年被掠往河南被遭痛苦。
南方人迷信凶兆吉祥,将毁坏的城址开辟成田冈,
新建的太原将十字街改成丁字路,然而,谁毁坏并州谁就跟着灭亡!
什么时候才是太平盛世哟,好让人看到朝廷重建晋阳。
注释
惠远祠:即晋祠,北宋熙宁中称晋祠为惠远祠。
西山:指晋祠背后的悬瓮山。
中原北门:晋阳是北方重镇,是中原地区的北大门。
想见:想见当时晋阳城巍巍高耸插入云端。
望川亭:在晋祠圣母殿后悬瓮山巅,北齐时所建。
系舟山:在太原市北百余里。
薛王:即刘继元,刘承钧养子,本姓薛,即王位后称薛王,公元979年降宋。
大夏门:晋阳城北门之一。太原古称大夏,故名。
唐明村:即唐明镇,今太原市旧城街以北至西羊市一带。
巨屏:指晋阳城为北方巨大屏障。
河洛:指中原一带为契丹、金、蒙铁骑蹂躏。
苍龙、玉虎:指晋阳城宫殿的雕饰物。金雀觚(gū)棱:喻雕物的精致和建筑的 高大。
死恨:宋灭北汉后,将太原四万居民从太原迁往洛阳。
南人:这句说宋朝统治者讲究迷信。
畚(běn)锸(chā):音本叉,指箩筐和铁锹。
开连岗:指来毁灭晋阳城之后,在唐明镇筑太原新城。
官街:宋朝统治者为了钉死太原龙脉,把太原街道建成丁字形。
渠:他,他们,指赵末统治者。
却到:等到。
官家:对皇帝的称呼。
参考资料:
创作背景
参考资料:
赏析
诗的前八句,写作者登上悬瓮山顶的望川享,鸟瞰眼前景色,美不胜收,并引触了深深盼感慨。惠远祠前的晋溪水,从悬瓮山麓汩汩流出,清澈透碧,水中绿萍嫩翠、锦鳞腾跃,掀起了一层层银白色的浪花;溪上的悬瓮山象一座巨大的卧屏,群峰竞秀,气势磅礴,草木葱郁,景象万千;这里风景优美,形势雄伟,是中原大地的北大门,当年的晋阳故城就座落在这里,可以想见那巍峨的城阙高耸入云,景象无比壮观。站在望川亭上,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兴衰变迁,感慨万端,如今眼前所展现出的,只有那千顷沃野上,一层层麦浪在春风中摇曳翻滚,那座悠久的历史故城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接着,次八句,诗人回顾了晋阳故城被赵宋统治者废毁的历史。保宁元年(969),宋太祖赵匡胤率兵进攻北汉,围困晋阳。在外敌入侵时,人民表现出积极御敌、浴血奋战、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“薜王出降民不降,屋瓦乱飞如箭簇”,就是晋阳人民面对侵略自发抵抗的爱国爱家精神的体现。然而城池被毁,生民被迁,河山虽然依旧形胜,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。“河洛几度风烟昏”,便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“中原北门”毁废后,给中原广大人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之灾。
此后八句又从宋朝毁灭晋阳文明古迹的角度予以鞭挞。“阙”指宫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。“觚棱”,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形。用“苍龙”“玉虎”“金雀”等词形容之,极显其金碧辉煌、凌云欲飞的景象气势。如此宏伟壮丽的古迹,竟被付之一炬,且将民居尽焚,以致“至今父老哭向天,死恨河南往来苦”。“往来”二字,概括了数百年来无数人民的辛酸,它不仅鞭挞了宋统治者给山西人民带来的灾难,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山西人民眷念故乡的传统。据传被掳至河南的山西人总不忘岁时回乡祭祀祖先,“往来”时还带些特产以充路资,此亦为晋商之渊源。“南人鬼巫”四句,则矛头直指宋王朝,斥其不重人事,迷信风水,导致了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”的可悲下场。
末二句乃全诗主旨所在,前面从军事、政治、文化的角度阐述利弊,旨在希望金统治者再振围威,重建晋阳。
全诗曲折往复,词语慷慨,气势雄放。抒发了强烈反对战争的情怀。
参考资料:
元好(hào)问(1190年8月10日—1257年10月12日),字裕之,号遗山,世称遗山先生。太原秀容(今山西忻州)人。金代著名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。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、文坛盟主,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,被尊为“北方文雄”、“一代文宗”。他擅作诗、文、词、曲。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,其“丧乱诗”尤为有名;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,可与两宋名家媲美;其散曲虽传世不多,但当时影响很大,有倡导之功。有《元遗山先生全集》、《中州集》。
余少时过里肆中,见北杂剧有《四声猿》,意气豪达,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,题曰“天池生”,疑为元人作。后适越,见人家单幅上有署“田水月”者,强心铁骨,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,字画之中,宛宛可见。意甚骇之,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。
一夕,坐陶编修楼,随意抽架上书,得《阙编》诗一帙。恶楮毛书,烟煤败黑,微有字形。稍就灯间读之,读未数首,不觉惊跃,忽呼石篑:“《阙编》何人作者?今耶?古耶?”石篑曰:“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。先生名渭,字文长,嘉、隆间人,前五六年方卒。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,即其人也。”余始悟前后所疑,皆即文长一人。又当诗道荒秽之时,获此奇秘,如魇得醒。两人跃起,灯影下,读复叫,叫复读,僮仆睡者皆惊起。余自是或向人,或作书,皆首称文长先生。有来看余者,即出诗与之读。一时名公巨匠,浸浸知向慕云。
文长为山阴秀才,大试辄不利,豪荡不羁。总督胡梅林公知之,聘为幕客。文长与胡公约:“若欲客某者,当具宾礼,非时辄得出入。”胡公皆许之。文长乃葛衣乌巾,长揖就坐,纵谈天下事,旁若无人。胡公大喜。是时公督数边兵,威振东南,介胄之士,膝语蛇行,不敢举头;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,信心而行,恣臆谈谑,了无忌惮。会得白鹿,属文长代作表。表上,永陵喜甚。公以是益重之,一切疏记,皆出其手。
文长自负才略,好奇计,谈兵多中。凡公所以饵汪、徐诸虏者,皆密相议然后行。尝饮一酒楼,有数健儿亦饮其下,不肯留钱。文长密以数字驰公,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,皆斩之,一军股栗。有沙门负资而秽,酒间偶言于公,公后以他事杖杀之。其信任多此类。
胡公既怜文长之才,哀其数困,时方省试,凡入帘者,公密属曰:“徐子,天下才,若在本房,幸勿脱失。”皆曰:“如命。”一知县以他羁后至,至期方谒公,偶忘属,卷适在其房,遂不偶。
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,遂乃放浪曲糵,恣情山水,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,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,沙起云行,风鸣树偃,幽谷大都,人物鱼鸟,一切可惊可愕之状,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,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,故其为诗,如嗔如笑,如水鸣峡,如种出土,如寡妇之夜哭,羁人之寒起。当其放意,平畴千里;偶尔幽峭,鬼语秋坟。文长眼空千古,独立一时。当时所谓达官贵人、骚士墨客,文长皆叱而奴之,耻不与交,故其名不出于越。悲夫!
一日,饮其乡大夫家。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,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,欲以苦之。文长援笔立成,竟满其纸,气韵遒逸,物无遁情,一座大惊。
文长喜作书,笔意奔放如其诗,苍劲中姿媚跃出。余不能书,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、文征仲之上。不论书法,而论书神:先生者,诚八法之散圣,字林之侠客也。间以其余,旁溢为花草竹石,皆超逸有致。
卒以疑杀其继室,下狱论死。张阳和力解,乃得出。既出,倔强如初。晚年愤益深,佯狂益甚。显者至门,皆拒不纳。当道官至,求一字不可得。时携钱至酒肆,呼下隶与饮。或自持斧击破其头,血流被面,头骨皆折,揉之有声。或槌其囊,或以利锥锥其两耳,深入寸余,竟不得死。
石篑言:晚岁诗文益奇,无刻本,集藏于家。予所见者,《徐文长集》、《阙编》二种而已。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,抱愤而卒。
石公曰:先生数奇不已,遂为狂疾;狂疾不已,遂为囹圄。古今文人,牢骚困苦,未有若先生者也。虽然,胡公间世豪杰,永陵英主,幕中礼数异等,是胡公知有先生矣;表上,人主悦,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。独身未贵耳。先生诗文崛起,一扫近代芜秽之习,百世而下,自有定论,胡为不遇哉?梅客生尝寄余书曰:“文长吾老友,病奇于人,人奇于诗,诗奇于字,字奇于文,文奇于画。”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。无之而不奇,斯无之而不奇也哉!悲夫!
六月二十六日,愈白。李生足下:生之书辞甚高,而其问何下而恭也。能如是,谁不欲告生以其道?道德之归也有日矣,况其外之文乎?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,焉足以知是且非邪?虽然,不可不为生言之。
生所谓“立言”者,是也;生所为者与所期者,甚似而几矣。抑不知生之志: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?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?蕲胜于人而取于人,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!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,则无望其速成,无诱于势利,养其根而俟其实,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实遂,膏之沃者其光晔。仁义之人,其言蔼如也。
抑又有难者。愈之所为,不自知其至犹未也;虽然,学之二十余年矣。始者,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,非圣人之志不敢存。处若忘,行若遗,俨乎其若思,茫乎其若迷。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,惟陈言之务去,戛戛乎其难哉!其观于人,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,犹不改。然后识古书之正伪,与虽正而不至焉者,昭昭然白黑分矣,而务去之,乃徐有得也。
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,汩汩然来矣。其观于人也,笑之则以为喜,誉之则以为忧,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,然后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惧其杂也,迎而距之,平心而察之,其皆醇也,然后肆焉。虽然,不可以不养也,行之乎仁义之途,游之乎诗书之源,无迷其途,无绝其源,终吾身而已矣。
气,水也;言,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。气之与言犹是也,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虽如是,其敢自谓几于成乎?虽几于成,其用于人也奚取焉?虽然,待用于人者,其肖于器邪?用与舍属诸人。君子则不然。处心有道,行己有方,用则施诸人,舍则传诸其徒,垂诸文而为后世法。如是者,其亦足乐乎?其无足乐也?
有志乎古者希矣,志乎古必遗乎今。吾诚乐而悲之。亟称其人,所以劝之,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。问于愈者多矣,念生之言不志乎利,聊相为言之。愈白。
玉笛一声天地愁,便觉梅花瘦。寒流清浅时,明月黄昏后,独醉一蹲桑落酒。
夜景
醺醺绮罗欢笑彻,檀板歌声歇。宝鼎串香绝,银烛灯花谢,玳筵前酒阑人散也。
情
描金翠钿侵鬓贴,满口儿喷兰麝。檀板撒红牙,皓齿歌白雪,定不定百般娇又怯。
【紫花儿】鬓丝禅榻,眉黛吟窗,扇影歌楼。献书北阙,挟策南州。迟留,
社燕秋鸿几回首。壮怀感旧,妩媚精神,罗绮风流。
【调笑令】渐久,过清秋,今古盟山惜未休。琴樽相对消闲昼,尽乌丝醉围
红袖。阳关一声人去后,消疏了月枕双讴。
【秃厮儿】浩浩寒波野鸥,消消夜雨兰舟,津亭送别风外柳。甚不解?系离
愁,悠悠。
【圣药王】夜气收,人语幽,西楼梦断月沉钩。惜胜游,忆唱酬,追思往事
到心头,肠欲断泪先流。
【尾】彩云冉冉巫山岫,还相逢邂逅绸缪。终日惜芳心,思量岁寒友。
 元好问
元好问 袁宏道
袁宏道 韩愈
韩愈 张可久
张可久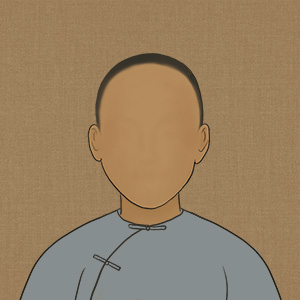 李邦基
李邦基 王国维
王国维 邓千江
邓千江 徐俯
徐俯 杨无咎
杨无咎 汪藻
汪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