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乡间农家欢欣鼓舞,喜乐自得,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,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。炎炎夏日,麦浪滚滚,夏粮丰收了。夏茧也丰收了,檐头缲车索索作响,野蚕作茧无人收取,只得自生自灭。一派丰收之景,但麦打成粮,蚕茧织成绢丝,乡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,而不得不把粮、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。在这丰收的年景里,他们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,织好的绢自己穿,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,以缴纳官府的横敛就行了。乡民们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,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
注释
男声欣欣女颜悦:此句运用了互文手法,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,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。其实无论男女,他们的声音,他们的容颜,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。
檐头:原指屋檐的边沿,此处应指屋檐下。缲车:即“缫车”,缫丝用的器具。
轴:此处指织绢的机轴。
黄犊:指小牛。
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,原作者已无法考证。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,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译文及注释二
译文
看着眼前丰收的景象,男人们的话语里充满了喜悦,女人们的脸上也洋溢着笑容,家家户户再也没有怨言,说的话也和往常不一样了。
虽然五月天气炎热,此时的麦风却给人以清凉的感觉。在村中的屋檐下,妇女们正忙着用缲车缫丝,缲车上发出一阵阵倾细的声音。
家蚕丰收,野蚕做的茧再也没有人来收取,于是这些茧在树上就变成了秋蛾,在树叶间扑扑地飞舞着。
麦子收割以后一筐一筐地堆放在麦场上,绢布织成后一匹一匹地缠在轴上,农民们可以确认今年的收成已足够缴纳官府的赋税了。
不指望还有入口的粮食,也不指望还有绢布剩下来做件衣服穿在身上,只是暂且可以免除去前往城中卖掉自己的小黄牛了。
农民家庭的衣食实在谈不上什么好与坏,只要家里人不被捉进县衙门,便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了。
注释
⑴欣欣:欢喜的样子。颜悦:脸上含笑。
⑵别:特别,例外。
⑶麦风:麦熟时的风,南风。
⑷索索:缫丝声。缲(sāo)车:也作“缫车”,抽丝的器具,因有轮旋转抽丝,故名。
⑸扑扑:象声词。此句是说野蚕无人要(因家蚕丰收)而在树上化为秋蛾。
⑹的知:确切知道。输:交纳赋税。
⑺望:一作“愿”。
⑻犊(dú):小牛,泛指耕牛。
⑼无厚薄:讲求不了好坏。
⑽县门:县衙门。
参考资料:
赏析
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,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。仲夏时节,农民麦、茧喜获丰收,却被官府劫一空,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,只能过着“衣食无厚薄”的悲惨生活。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,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,相当具有典型性。全诗四换韵脚。依照韵脚的转换,诗可分为四个层次。
前两句为第一层,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:“男声欣欣女颜悦,人家不怨言语别。”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、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,说话也温和悦人。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,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,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。其实无论是男是女,他们的声音,他们的容颜,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,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,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。先写农家喜乐自得,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,由此造成悬念,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。
三、四、五、六这四句为第二层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,是因为夏粮、夏茧丰收,有了一个好收成。“五月”二句,写织妇因为喜悦,面对五月艳阳,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,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。五月麦风清,写夏粮丰收;檐头缲车索索作响,写夏茧丰收。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,诗人又从侧面下笔:“野蚕作茧人不取,叶间扑扑秋蛾生。”这两句写家蚕丰收,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,以至野蚕化蛾,在桑叶上飞来飞去。野蚕作茧无人收取,自生自灭,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,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。在这一层次里,作者一写收麦,一写缲丝,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,突出丰收的景象,使一、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。后面三句:“麦收上场绢在轴”,“不望入口复上身”,“田家衣食无厚薄”,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,或抒情,或议论,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。
七、八、九、十这四句为第三层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,感情则由喜转悲,形成一个大的波澜,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,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。“麦收上场绢在轴,的知输得官家足”,写麦、茧丰收的结果。“轴”,指织绢的机轴。丰收,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,事实却非如此。麦打成粮,蚕茧织成绢丝,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,而不得不把粮、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。“的知”一句为神来之笔。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,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,刻画得维妙维肖。“不望”两句,更为沉痛。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,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,织好的绢自己穿,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,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。那么,农民自己吃什么,穿什么,是可以想见的。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,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。
最后两句为第四层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,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。但这种揭露,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,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,让读者思而得之。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,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,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。
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,颇具特色。在一般的作品中,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,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。这首诗则不然。《田家行》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、蚕茧丰收,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。但丰收的结果,并不是生活的改善,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,生活依然悲惨,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。这种遭遇,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,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,如此选材,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。
在表现方法上,古乐府多叙事,《田家行》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,一是麦、茧丰收,一是粮、绢大部输官,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。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,语言质朴无华,通俗流畅、凝炼精警,于平易中见深刻。
参考资料:
创作背景
参考资料:
王建(768年—835年),字仲初,颍川(今河南许昌)人,唐朝诗人。出身寒微,一生潦倒。曾一度从军,约46岁始入仕,曾任昭应县丞、太常寺丞等职。后出为陕州司马,世称王司马。与张籍友善,乐府与张齐名,世称张王乐府。
损之在我左,顺之在我右。
云是二月天,春风出携手。
同过靖安里,下马寻元九。
元九正独坐,见我笑开口。
还指西院花,乃开北亭酒。
如言各有故,似惜欢难久。
神合俄顷间,神离欠申后。
觉来疑在侧,求索无所有。
残灯影闪墙,斜月光穿牖。
天明西北望,万里君知否?
老去无见期,踟蹰搔白首。
江北之山,蜿蜒磅礴,连亘数州,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,皆在吾县。县治枕山而起,其外林壑幽深,多有园林池沼之胜。出郭循山之麓,而西北之间,群山逶逦,溪水潆洄,其中有径焉,樵者之所往来。数折而入,行二三里,水之隈,山之奥,岩石之间,茂树之下,有屋数楹,是为潘氏之墅。余褰裳而入,清池湫其前,高台峙其左,古木环其宅。于是升高而望,平畴苍莽,远山回合,风含松问,响起水上。噫!此羁穷之人,遁世远举之土,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,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。
夫科目之贵久矣,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,中于膏盲,人于肺腑,群然求出于是,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。其失者,未必其皆不才;其得者,未必其皆才也。上之人患之,于是博搜遍采,以及山林布衣之士,而士又有他途,捷得者往往至大官。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,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。有司者,好恶与人殊,往往几得而复失。一旦弃去,专精覃思,尽究百家之书,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,世莫不知有先生。间者求贤之令屡下,士之得者多矣,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,混迹于田夫野老,方且乐而终身,此岂徒然也哉?
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,方浮沉世俗之中,未克遂意,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,乃为记之。
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:草木之无声,风挠之鸣。水之无声,风荡之鸣。其跃也,或激之;其趋也,或梗之;其沸也,或炙之。金石之无声,或击之鸣。人之于言也亦然,有不得已者而后言。其歌也有思,其哭也有怀,凡出乎口而为声者,其皆有弗平者乎!
乐也者,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,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。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者,物之善鸣者也。维天之于时也亦然,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。是故以鸟鸣春,以雷鸣夏,以虫鸣秋,以风鸣冬。四时之相推敚,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?
其于人也亦然。人声之精者为言,文辞之于言,又其精也,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。其在唐、虞,咎陶、禹,其善鸣者也,而假以鸣,夔弗能以文辞鸣,又自假于《韶》以鸣。夏之时,五子以其歌鸣。伊尹鸣殷,周公鸣周。凡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,皆鸣之善者也。周之衰,孔子之徒鸣之,其声大而远。传曰: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其弗信矣乎!其末也,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。楚,大国也,其亡也以屈原鸣。臧孙辰、孟轲、荀卿,以道鸣者也。杨朱、墨翟、管夷吾、晏婴、老聃、申不害、韩非、慎到、田骈、邹衍、尸佼、孙武、张仪、苏秦之属,皆以其术鸣。秦之兴,李斯鸣之。汉之时,司马迁、相如、扬雄,最其善鸣者也。其下魏晋氏,鸣者不及于古,然亦未尝绝也。就其善者,其声清以浮,其节数以急,其辞淫以哀,其志弛以肆;其为言也,乱杂而无章。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?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!
唐之有天下,陈子昂、苏源明、元结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观,皆以其所能鸣。其存而在下者,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。其高出魏晋,不懈而及于古,其他浸淫乎汉氏矣。从吾游者,李翱、张籍其尤也。三子者之鸣信善矣。抑不知天将和其声,而使鸣国家之盛邪,抑将穷饿其身,思愁其心肠,而使自鸣其不幸邪?三子者之命,则悬乎天矣。其在上也奚以喜,其在下也奚以悲!东野之役于江南也,有若不释然者,故吾道其于天者以解之。
碑者,悲也。古者悬而窆,用木。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,因留之不忍去,碑之名由是而得。自秦汉以降,生而有功德政事者,亦碑之,而又易之以石,失其称矣。余之碑野庙也,非有政事功德可纪,直悲夫甿竭其力,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!
瓯越间好事鬼,山椒水滨多淫祀。其庙貌有雄而毅、黝而硕者,则曰将军;有温而愿、晰而少者,则曰某郎;有媪而尊严者,则曰姥;有妇而容艳者,则曰姑。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,峻之以陛级。左右老木,攒植森拱,萝茑翳于上,鸱鸮室其间。车马徒隶,丛杂怪状。甿作之,甿怖之,走畏恐后。大者椎牛;次者击豕,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。牲酒之奠,缺于家可也,缺于神不可也。不朝懈怠,祸亦随作,耄孺畜牧栗栗然。疾病死丧,甿不曰适丁其时耶!而自惑其生,悉归之于神。
虽然,若以古言之,则戾;以今言之,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。何者?岂不以生能御大灾,捍大患,其死也则血良于生人。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,是戾于古也明矣。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,温愿而少者有之,升阶级,坐堂筵,耳弦匏,口粱肉,载车马,拥徒隶者皆是也。解民之悬,清民之暍,未尝怵于胸中。民之当奉者,一日懈怠,则发悍吏,肆淫刑,驱之以就事,较神之祸福,孰为轻重哉?平居无事,指为贤良,一旦有大夫之忧,当报国之日,则佪挠脆怯,颠踬窜踣,乞为囚虏之不暇。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,又何责其真土木耶?故曰:以今言之,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。
既而为诗,以纪其末:土木其形,窃吾民之酒牲,固无以名;土木其智,窃吾君之禄位,如何可仪!禄位颀颀,酒牲甚微,神之享也,孰云其非!视吾之碑,知斯文之孔悲!
翠蛾恨谁?青鸾信迟,题诗记清明日。泪弹红雨笑邻姬,同立苍苔地。萼绿仙人,玄都观里,怪刘郎不记得。今春又归,花能几回?且自吹笙醉。
访九皋使君
槿篱,傍水,楼与青山对。一庭香雪糁荼蘼,松下溪童睡。净地留题,柴门还闭,笼开鹤自飞。看梅,未回,多管向西湖醉。
春思
菱花破两边,瑶琴断四弦,恩又翻成怨。黄云孤雁褪花钿,羞掩双鸾扇。归燕年年,离恨绵绵,又西湖拜扫天。寺前,上船,试照我伤春面。
 王建
王建 白居易
白居易 戴名世
戴名世 韩愈
韩愈 陆龟蒙
陆龟蒙 张可久
张可久 晏几道
晏几道 辛弃疾
辛弃疾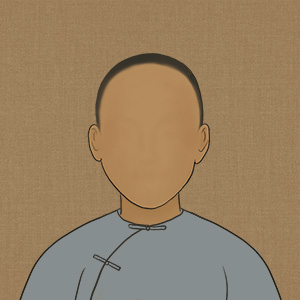 王质
王质 陈允平
陈允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