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繁茂枝头,梅花飘落千万片,落时犹多情,学着雪花随风转。昨夜歌舞草草散,酒醒又添愁无限。
楼上清寒,寒山围四面,大雁过尽暮霭深深漫。半晌凭栏不见人,罗帕掩泪把他思量遍。
注释
鹊踏枝:即《蝶恋花》,原唐教坊曲名,商调曲。又名《黄金缕》《凤栖梧》《卷珠帘》《一箩金》。其用为词牌始于宋。双调六十字,前后片各四仄韵。
笙(shēng)歌:吹笙唱歌。容易:轻易。
征鸿:远行的大雁。征鸿过尽,昭示着节令的转换。
“暮景”句:远处近处,只有浓浓淡淡的烟霭装点着无边的暮色。
一晌:表示时间,有片刻多时二意。
鲛绡(jiāo xiāo):传说是南海鲛人所织之绡,这里指精美的手帕。掩(yǎn)泪:掩面而泣。
参考资料:
赏析
上半阕开端“梅落繁枝千万片,犹自多情,学雪随风转”,仅只三句,便写出了所有有情之生命面临无常之际的缝缝哀伤,这正是人世千古共同的悲哀。首句“梅落萦枝千万片”,颇似杜甫《曲江》诗之“风飘万点正愁人”。然而杜甫在此七字之后所写的乃是杯且看欲尽花经眼”,是则在杜甫诗中的万点落花不过仍为看花之诗人所见的景物而已;可是正中在“梅落繁枝”七字之后,所写的则是“犹自多情,学雪随风转”,是正中笔下的千万片落花已不仅只是诗人所见的景物,而俨然成为一种陨落的多情生命之象喻了。而且以“千万片”来写此一生命之陨落,其意象乃是何等缤纷,又何等凄哀,既足可见陨落之无情,又足可见临终之缱绻,所以下面乃径承以“犹自多情”四字,直把千万片落花视为有情矣。至于下面的“学雪随风转”,则又颇似李后主词之“落梅如雪乱”。然而后主的“落梅如雪”,也不过只是诗人眼前所见的景物而已,是诗人所见落花之如雪也;可是正中之“学雪随风转”句,则是落花本身有意去学白雪随风之双转,其本身就表现着一种多情缱绻的意象,而不仅是写实的景物了。这里所写的不是感情之事迹,而表达的却是感情之境界。所以上三句虽是写景,却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动人的多情之生命陨落的意象。下面的“昨夜笙歌容易散,酒醒添得愁无限”二句,才开始正面叙写人事,而又与前三句景物所表现之意象遥遥相应,笙歌之易散正如繁花之易落。花之零落与人之分散,正是无常之人世之必然的下场,所以加上”容易”两个字,正如晏小山词所说的“春梦秋云,聚散真容易”也。面对此易落易散的短哲无常之人世,则有情生命之哀伤愁苦当然乃是必然的了,所以落花既随风飘转,表现得如此缱绻多情,而诗人也在歌散酒醒之际添得无限哀愁矣。“昨夜笙歌”二句,虽是写的现实之人事,可是在前面“梅落繁枝”三句景物所表现之意象的衬托下,这二句便俨然也于现实人事外有着更深、更广的意蕴了。
下半阕开端之“楼上春山寒四面”,正如后一首《鹊踏枝》之“河畔青芜”,也是于下半阕开端时突然荡开作景语。正中词往往忽然以闲笔点缀一二写景之句,极富俊逸高远之致,这正是《人间词话》之所以从他的一贯之“和泪试严妆”的风格中,居然着出了有韦苏州、孟襄阳之高致的缘故。可是正中又毕竟不同于韦、孟,正中的景语于风致高俊以外,其背后往往依然含蕴着许多难以言说的情意。即如后一首之“河畔青芜堤上柳”,表面原是写景,然而读到下面的“为间新愁,何事年年有”二句,才知道年年的芜青、柳绿原来正暗示着年年在滋长着的新愁。这一句的“楼上春山寒四面”,也是要等到读了下面的“过尽征鸿,暮景烟深浅”二句,才能体会出诗人在楼上凝望之久与怅惘之深,而且“楼上”已是高寒之所,何况更加以四面春山之寒峭,则诗人之孤寂凄寒可想,而“寒”字下更加上了“四面”二字,则诗人的全部身心便都在寒意的包围侵袭之下了。以外表的风露体肤之寒,写内心的凄寒孤寂之感,这也正是正中一贯所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,即如后一首之“独立小桥风满袖”、此一首之“楼上春山寒四面”及《抛球乐》之“风人罗衣贴体寒”,便都能予读者此种感受和联想。接着说“过尽征鸿”,不仅写出了凝望之久与瞻望之远,而且征鸿之春来秋去,也最容易引人想起踪迹的无定与节序的无常。而诗人竟在“寒四面”的“楼上”,凝望这些漂泊的“征鸿”直到“过尽”的时候,则其中心之怅惘哀伤,不言可知矣。然后承之以“暮景烟深浅”五个字,“深浅”二字,正写出暮烟因远近而有浓淡之不同,既曰“深浅”,于是而远近乃同在此一片暮烟中矣。这五个字不仅写出了一片苍然的暮色,更写出了高楼上对此苍然暮色之人的一片怅惘的哀愁。于此,再反顾前半阕的“梅落繁枝”三句,因知“梅落”三句,固当是歌散酒醒以后之所见,而此“楼上春山”三句,实在也当是歌散酒醒以后之所见;不过,“梅落”三句所写花落之情景极为明白清晰,故当是白日之所见,至后半阕则自“过尽征鸿”表现着时间消逝之感的四个字以后,便已完全是日暮的景色了。从白昼到日暮,诗人为何竟在楼上凝望至如此之久,于是结二句之“一晌凭栏人不见,鲛绡掩泪思量遍”,便完全归结到感情的答案来了。“一晌”二字,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解释为“指示时间之辞,有指多时者,有指暂时者”,引秦少游《满路花》词之“未知安否,一晌无消息”,以为乃“许久”之义,又引正中此句之“一晌凭栏”,以为乃“霎时”之义。私意以为“一晌”有久、暂二解是不错的,但正中此句当为“久”意,并非“暂”意,张相盖未仔细寻味此词,故有此误解也。
综观这首词,如上所述,既自白昼景物直写到暮色苍然,则诗人凭栏的时间之久当可想见,故曰“一晌凭栏”也。至于何以凭倚在栏杆畔如此之久,那当然乃是因为内心中有一种期待怀思的感情的缘故,故继之曰“人不见”,是所思终然未见也。如果是端己写人之不见,如其《荷叶杯》之“花下见无期”、“相见更无因”等句,其所写的便该是确实有他所怀念的某一具体的人;而正中所写的“人不见”,则大可不必确指,其所写的乃是内心寂寞之中常如有所期待怀思的某种感情之境界,这种感情可以是为某人而发的,但又并不使读者受任何现实人物的拘限。只因为端己在写“人不见”时,同时所写的乃是“记得那年花下”及“绝代佳人难得”等极现实的情事;而正中在写“人不见”时,同时所写的则是春山四面之凄寒与暮烟远近之冥漠。端己所写的,乃是现实这情事;而正中所表现的,则是一片全属于心灵上的怅惘孤寂之感。所以正中词中“人不见”之“人”是并不必确指的。可是,人虽不必确指,而其期待怀思之情则是确有的,故结尾一句乃曰“鲛绡掩泪思量遍”也。“思量”而曰“遍”,可见其怀思之情始终不解,又曰“掩泪”,可见其怀思之情悲苦哀伤。曰“鲛绡”,一则可见其用以拭泪之巾帕之珍美,再则用泣泪之人所织之绡巾来拭泪,乃愈可见其泣泪之堪悲,故曰“鲛绡掩泪思量遍”也。其实正中此词,原来所写的乃是一种感情之境界,而并未实写感情之事迹。
全词充满了象喻之意味,因此末句之为男子口吻抑为女子口吻,实在无关紧要,何况美人、香草之托意,自古而然,“鲛绡掩泪’‘一句,主要的乃在于这几个字所表现的一种幽微珍美的悲苦之情意,这才是读者所当用心去体味的。这种一方面写自己主观之情意,而一方面又表现为托喻之笔法,与端己之直以男子之口吻来写所欢的完全写实之笔法,当然是不同的。
参考资料:
创作背景
参考资料:
冯延巳 (903--960)又名延嗣,字正中,五代广陵(今江苏省扬州市)人。在南唐做过宰相,生活过得很优裕、舒适。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辞,文人的气息很浓,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较大的影响。宋初《钓矶立谈》评其“学问渊博,文章颖发,辩说纵横”,其词集名《阳春集》。
樽前有人颜似玉,笑索多情句。歌残林叶飞,舞罢庭花妒,冰弦一霎秋夜雨。东
风又来供暮愁,吹上蛾眉皱。应知弄玉心,相道东阳瘦,花落燕飞人病酒。
 冯延巳
冯延巳 白居易
白居易 李致远
李致远 范仲淹
范仲淹 向滈
向滈 孙光宪
孙光宪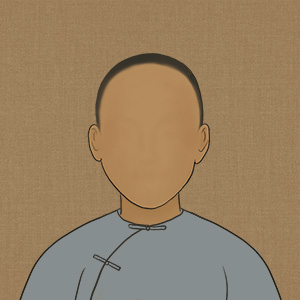 段克己
段克己 王国维
王国维 刘克庄
刘克庄 白朴
白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