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春风最先试着让梅花吐出嫩嫩的花蕊。花瓶中的梅花姿色美丽,冷韵幽香,伴随着它的是明沙净水。它不卑不亢,从容自如,不能被其他花儿理解,应当与月亮约定日期来作伴。
它的香气清幽淡雅,传得很远,总是先在女子们的钗头上出现。大雪过后。梅花被王母宴请到瑶池,这是人世间报春的第一枝花。
注释
试手:尝试身手。
頩(pīng)姿:美丽的姿色。頩,面目光泽艳美。
明沙水:明净的沙水。
端须:只该。
期:约定之时。
钗(chāi)头:妇女的头饰,多为金玉器。
燕:通“宴”,宴会。这里指举办宴会。
瑶池:神话传说中西王母居住的仙境,有玉楼十二层。▲
赏析
词的起句奇绝。春风吹绽百花,这是很普通的比喻修辞,把春风之吹拂说成春风之手的抚摸,这也是很常见的拟人修辞,但是此词作者把这两者融合,再加入了他独有的体会之后,一句“春风试手先梅蕊”就显得异常新颖了。“试手”二字仿佛是说春风吹绽百花的这门“技艺”需要先操练一下,而操练的结果则是使梅花先于百花开出了花蕊。冬去春来,春风自然要启开冰封的万物,但它却独钟情于梅花,暗含着对梅花的赞颂。“頩姿冷艳明沙水”一句以外在写内质。“颍姿”是写梅花美丽的姿容,“冷艳”写花色,这都是暗指它清高幽独的气质。“明沙水”是它生长的环境,这冰清玉洁、一尘不染的环境,正是为了凸显梅花的高洁。
三、四句以梅花与百花对比。陆游《卜算子·咏梅》曾写梅花“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”,梅花主动地不与百花争艳却遭来百花的妒忌,把梅花写得极为美丽又清高孤绝。而此词的作者却说“不受众芳知”,梅花孤高的气势削减了,仿佛还有了一丝落魄的哀伤。然而这只是铺垫,是作者刻意地压抑感情,接着”端须”一句就开始高扬——梅花之清高孤绝唯有月亮能与之相配。这感情和气势已丝毫不让陆游之词。这种先抑后扬的写法,使全词结构显得很精致。
下阕开始写梅花与人的互动。“清香闲自远”句写梅花的幽香,已暗含着闻到花香的人。正因为花香清雅而幽远,因此女子纷纷把梅花装饰在头发上,一个“先”字再次强调了它与“众芳”的区别。“雪后燕瑶池”一句想象瑰丽,瑶池已自高远华美,更加“雪后”修饰,一种幽冷清空的气氛更加强烈。而梅花因其高洁的品格和气质,被邀请到这样的地方赴宴,又荣列人间众芳之首,这是何等的荣耀。这一想象的目的还是从另一个角度赞美梅花与众不同的气质和“仙姿”。
整首词始终围绕梅花来写。无论是比喻、拟人还是想象,目的都是为了赞誉梅花的各种品格。赵令畴因与苏轼交好而入党籍,一生仕途坎坷,此词虽表面上只是写梅花的品格.但未尝不是以梅花自喻,寄托作者深沉的感情。▲
创作背景
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植梅的繁盛时期,咏梅的作品也很多。赵令畴的这首《菩萨蛮》同样是借梅花以寓性情,寄托深远,非徒然咏梅。词人性情中的那份孤傲与傲雪的梅花极为相近,于是便借梅花表达自己的心境。
赵令畤(1061~1134)初字景贶,苏轼为之改字德麟,自号聊复翁。太祖次子燕王德昭﹝赵德昭﹞玄孙。元祐中签书颍州公事,时苏轼为知州,荐其才于朝。后坐元祐党籍,被废十年。绍兴初,袭封安定郡王,迁宁远军承宣使。四年卒,赠开府仪同三司。著有《侯鲭录》八卷,赵万里为辑《聊复集》词一卷。
经,常道也,其在于天谓之命,其赋于人谓之性,其主于身谓之心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,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;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是常道也,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,一也;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,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,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;《书》也者,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;《诗》也者,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;《礼》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;《乐》也者,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;《春秋》也者,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,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,所以尊《易》也;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,所以尊《书》也;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,所以尊《诗》也;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。所以尊《礼》也;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,所以尊《乐》也;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,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,犹之富家者之父祖,虑其产业库藏之积,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,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,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,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,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,吾心之记籍也;而六经之实,则具于吾心,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,具存于其家;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,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,牵制于文义之末,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;是犹富家之子孙,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,日遗忘散失,至于窭人丐夫,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。曰: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!”何以异于是?
呜呼!六经之学,其不明于世,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,崇邪说,是谓乱经;习训诂,传记诵,没溺于浅闻小见,以涂天下之耳目,是谓侮经;侈淫辞,竞诡辩,饰奸心盗行,逐世垄断,而犹自以为通经,是谓贼经。若是者,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,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?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,在卧龙西岗,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,既敷政于民,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,将进之以圣贤之道,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;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,曰:经正则庶民兴,庶民兴斯无邪慝矣。阁成,请予一言,以谂多士。予既不获辞,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!世之学者,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,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】残云剩雨阳台上,空赢得两袖余香。则恐怕春夜长,东风壮,桃花飘荡,何处
觅刘郎? 九日渡江二首
秋风江上棹孤舟,烟水悠悠。伤心无句赋登楼,山容瘦,老树替人愁。【幺
】樽前醉把茱萸嗅,问相知几个白头。乐可酬,人非旧,黄花时候,难比旧风流。
秋风江上棹孤航,烟水茫茫。白云西去雁南翔,推篷望,清思满沧浪。【幺】东
篱载酒陶元亮,等档间过了重阳。自感伤。何情况,黄花惆怅,空作去年香。 扬子江阻风
篷窗风急雨丝丝,闷捻吟髭。维扬西望渺何之?无一个鸿鳞至,把酒问篙师。
【幺】他迎头儿便说干戈事,待风流再莫追思。塌了酒楼,焚了茶肆,柳营花市,
更说甚呼燕子唤莺儿。 代人寄情
花下清歌月下弹,意惹情关。颠鸾倒凤数十番,从分散,情意便阑珊。【幺
】我家私虽不比王十万,论声名索另眼儿相看。更做道姐姐奸,恁须是婆婆惯,
少甚么南来鱼雁,直不得两字问平安。 上已日登姚江龙泉寺分韵得暗字
天风吹我上岩,正值春三。残红飞絮点松杉,轻摇撼,无数落青衫。【幺
】登临未了斜阳暗,借白云半榻禅龛。发笑谈,论经谶,老龙惊惮,拖雨过江南。 咏雪效苏禁体作
天低风静日昏昏,一片同云。穿帘透暮舞纷纷,寒成阵,则索闭柴门。【幺
】陶学士满口誉清俊,邮亭中冻得来伤神,颠倒说老党村。诸般□,羊羔美耐,
金帐里醉醺醺。黄昏微雨净尘沙,飞尽归鸦。斜飘乱撒扑窗纱,迷鸳瓦,一色净
无瑕。【幺】棱棱衾铁萧萧塌,问羊羔那里寻他。不由人狂兴发,把扁舟驾,向
山阴直下,认不得戴逵家。 太真
开元天子好奢华,太真妃选作浑家。东风吹动祸根芽,娘牵挂,没乱煞胖娃
娃。【幺】不提防变却承平卦,闹渔阳一片胡笳。辞风榻,迁鸾驾,马嵬坡下,
踏碎海棠花。 丽华
临风阁内俏人儿,天生得玉骨冰姿。承欢奉喜度芳时,多才思,举笔便题诗。
【幺】谁承望擒虎将军至,拥貔貅百万雄师。惊散了玉树歌,推上云阳市。黄天
何事,流泪洒胭脂。
【幺篇】支楞弦断了绿绮琴,王吉玎掂折了碧玉簪,嗨,堕落了题桥志;吁,阑珊了解佩心。走将来笑吟吟,妆呆妆婪,硬厮挣软厮禁。泥中刺绵里针,黑头虫黄口岑鸟。
【凤鸾吟】自古到今,恩多须怨深。你说的牙疼誓,不害碜!有酒时唫,有饭时啃,你来我跟前委实图甚?小的每声价儿亻些,身材儿婪,请先生别觅个知音。
【柳叶儿】走将来乜斜头撒唚,不熨贴性儿希林,软处捏硬处掐甜处渗。休忒恁,莫沉吟,休辜负了柳影花阴。
【大石调】雁传书
春归后,柳丝难挽别离情。一片花飞减却春,对东风无语销魂。伤情,花飞泪落堕红雨,苍苔上海棠堆径。愁无尽,怕的是梨花庭院,风雨黄昏。
【明妃曲】愁闻,是谁家风前笛韵?梅花吹落江城。难禁,吹出了断肠声,到惹得月愁人病。鹃啼春思月中魂,花迷蝶梦窗前影。恹恹病,这相思能终得几个黄昏。
【秋海棠】谁似你辜恩?谁似我痴心?负心的上有神明,到如今参不透薄情心性。好姻缘整日重盟,恶姻缘番成画饼。多愁闷,消磨了白昼,顿送黄昏。
【比目鱼】数归期,掏得指头疼;盼归期,望断越山云。泪珠,泪珠滴尽湘江满,只落得暗里自沉吟。从今,再不去梦里搜寻,再不去愁中加病,再不去挂肚牵心。泪痕销夜烛,军被拥鸡声。捱过了几番寂寞.几度黄昏。
【余文】从今打破风流阵,一句句从头自忖。一任他朝朝暮暮,白昼黄昏。
滔滔春水东流,天阔云闲,树渺禽幽。山远横眉,波平消雪,月缺沉钩。桃蕊红妆渡口,梨花白点江头。何处离愁,人别层楼,我宿孤舟。
咏蟠梅
梨雪旋绕东风,谁屈冰梢,怪压苍松?绿萼含香,枯根层结,春信重封。清味远嫌蝶妒蜂,老枝寒舞凤蟠龙。夜月朦胧,疏蕊纵横;瘦影交加,碎玉玲珑。
二色鞋儿
轻摇环佩丁东,半露新荷,半掩芙蓉。花柳些些,霞绡点点,锦翠弓弓。绿绫扇轻拈落红,茜萝尖微印苔踪。心恨难通,裙底鸳鸯,出落雌雄。
 赵令畤
赵令畤 张衡
张衡 王守仁
王守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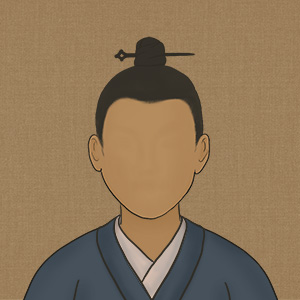 汤舜民
汤舜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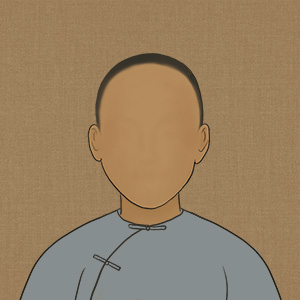 王举之
王举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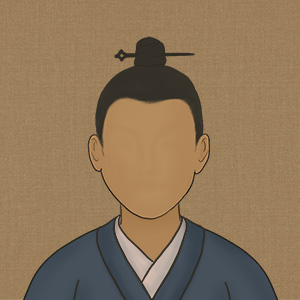 王元鼎
王元鼎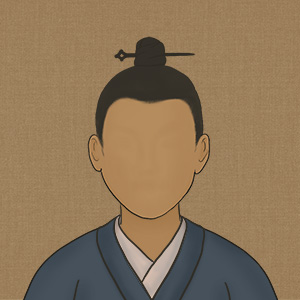 周文质
周文质 乔吉
乔吉 晏殊
晏殊 朱彝尊
朱彝尊 陈亮
陈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