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游乌龙潭记
予初游潭上,自旱西门左行城阴下,芦苇成洲,隙中露潭影。七夕再来,又见城端柳穷为竹,竹穷皆芦,芦青青达于园林。后五日,献孺召焉。止生坐森阁未归,潘子景升、钟子伯敬由芦洲来,予与林氏兄弟由华林园、谢公墩取微径南来,皆会于潭上。潭上者,有灵应,观之。
冈合陂陀,木杪之水坠于潭。清凉一带,坐灌其后,与潭边人家檐溜沟勺入浚潭中,冬夏一深。阁去潭虽三丈余,若在潭中立;筏行潭无所不之,反若往水轩。潭以北,莲叶未败,方作秋香气,令筏先就之。又爱隔岸林木,有朱垣点深翠中,令筏泊之。初上蒙翳,忽复得路,登登至冈。冈外野畴方塘,远湖近圃。宋子指谓予曰:“此中深可住。若冈下结庐,辟一上山径,頫空杳之潭,收前后之绿,天下升平,老此无憾矣!”已而茅子至,又以告茅子。
是时残阳接月,晚霞四起,朱光下射,水地霞天。始犹红洲边,已而潭左方红,已而红在莲叶下起,已而尽潭皆頳。明霞作底,五色忽复杂之。下冈寻筏,月已待我半潭。乃回篙泊新亭柳下,看月浮波际,金光数十道,如七夕电影,柳丝垂垂拜月。无论明宵,诸君试思前番风雨乎?相与上阁,周望不去。适有灯起荟蔚中,殊可爱。或曰:“此渔灯也。”
译文及注释
译文
我第一次游览乌龙潭,从旱西门(南京城门)向左走到城北边,那里芦苇就像一片小岛,芦苇的缝隙中露出潭水的影子。我在七夕节再来,又看到城的尽头柳树完了是竹林,竹林尽头是芦苇,芦苇青青直到园林。又过了五天,我的朋友宋献孺邀请我。茅元仪(字止生)住在森阁没有回去,潘之恒(字景升)、钟惺(字伯敬)从芦苇荡上来,我和林家兄弟从华林园、谢公墩走小路从南边来,都相逢在乌龙潭上。潭上有灵气,我们共同观赏。
山岗倾斜,树梢上的水滴掉进潭里。清凉山就像一条带子,坐落在乌龙潭的后边,和潭边人家的屋檐的排水槽、下水沟伸入深潭中,冬夏水一样深。楼阁离潭虽然三丈多,就像在潭水中耸立;竹筏在潭水中行走不管哪儿都能到达,倒像去水上楼阁。潭水北部,荷叶还没有凋残,正散发着秋天的香气,于是我们让竹筏先去那里。又喜欢隔岸的树林,有红色的墙点缀在深绿色中,于是让竹筏靠岸。刚上岸时土地全被草木覆盖,忽然找到一条路,沿路向上走到了山岗。山岗外边是田野池塘,远处有湖近处有苗圃。宋献孺指着这些对我说:“这个地方很适合居住。如果在山下建造一座房屋,开辟一条上山的路,俯视空旷的潭水,观赏前后的绿色景致,天下太平,在这里终老一生都没有遗憾了!”不一会茅元仪到了,他又把这话告诉了茅元仪。
这时候夕阳和月亮同时在天上,晚霞在四方升起,红光照下来,底下是水上面是霞。开始只照红了芦苇荡的边上,不一会潭水的左边也红了,又不一会红光照到了莲叶底下,再不一会全潭都红了。明亮的霞光作底色,五种颜色忽然又掺杂进来。下山找竹筏,月光已经布满半个潭面等着我们了。于是撑着竹篙停在新亭的柳树下面,观赏月光在水波中沉浮,金色的水光好几十道,就像七夕节雷电的光影,柳条下垂碰触水中的月亮。不管今天晴朗的夜晚,各位能否想到上次有乌龙潭的那番风雨吗?我们一起登上楼阁,向四周眺望不愿离去。正好有灯光在茂密的草丛树林里亮起,非常可爱。有人说:“这是渔灯。”
注释
旱西门:南京城门名,又称清凉门。
献孺:姓宋,作者之友。
止生:茅元仪,字止生。
森阁:茅元仪所建,在乌龙潭附近。
景升:潘之恒,字景升。
伯敬:钟惺,字伯敬。
华林园:南京园林。原为三国时东吴宫苑。
谢公墩:原为晋谢安园池。地近钟山。
陂陀:倾斜。
木杪:树梢。
清凉:清凉山。
浚:深。
蒙翳:此指草木覆盖。
结庐:构建房子。
頫:低头。同“俯”。
頳:红色。
新亭:茅元仪在乌龙潭建的亭子。
电影:雷电之光影。七夕电影:指作者二游乌龙潭遇雷雨时情形。
前番风雨:指二游乌龙潭事。
荟蔚:茂密的草丛树林。▲
简析
这篇游记选自《谭友夏合集》卷十一。文章描述了作者与好友第三次游乌龙潭的经历,先写山林与潭水相接的幽深境界,继而写晚霞映潭和月色照潭的奇妙景色。全文生趣盎然,可以说是逐层点染,极写乌龙潭晴日间多姿多彩之美。这与二游乌龙潭时风雨大作的景象形成了有趣的对比。
(1586—1637)明湖广竟陵人,字友夏。天启七年乡试第一。后赴京试,卒于旅店。善诗文,名重一时,与钟惺同为竟陵派创始者。论文强调性灵,反对摹古,追求幽深孤峭,所作亦流于僻奥冷涩。曾与钟惺共评选《唐诗归》、《古诗归》。自著有《岳归堂集》、《谭友夏合集》等。
孤始举孝廉,年少,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,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,欲为一郡守,好作政教,以建立名誉,使世士明知之;故在济南,始除残去秽,平心选举,违迕诸常侍。以为强豪所忿,恐致家祸,故以病还。
去官之后,年纪尚少,顾视同岁中,年有五十,未名为老。内自图之,从此却去二十年,待天下清,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时归乡里,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,欲秋夏读书,冬春射猎,求底下之地,欲以泥水自蔽,绝宾客往来之望。然不能得如意。
后徵为都尉,迁典军校尉,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,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,然后题墓道言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,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难,兴举义兵。是时合兵能多得耳,然常自损,不欲多之;所以然者,多兵意盛,与强敌争,倘更为祸始。故汴水之战数千,后还到扬州更募,亦复不过三千人,此其本志有限也。
后领兖州,破降黄巾三十万众。又袁术僭号于九江,下皆称臣,名门曰建号门,衣被皆为天子之制,两妇预争为皇后。志计已定,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,露布天下,答言“曹公尚在,未可也”。后孤讨禽其四将,获其人众,遂使术穷亡解沮,发病而死。及至袁绍据河北,兵势强盛,孤自度势,实不敌之;但计投死为国,以义灭身,足垂于后。幸而破绍,枭其二子。又刘表自以为宗室),包藏奸心,乍前乍却,以观世事,据有当州,孤复定之,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,人臣之贵已极,意望已过矣。
今孤言此,若为自大,欲人言尽,故无讳耳。设使国家无有孤,不知当几人称帝,几人称王!或者人见孤强盛,又性不信天命之事,恐私心相评,言有不逊之志,妄相忖度,每用耿耿。齐桓、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,以其兵势广大,犹能奉事周室也。《论语》云:“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殷,周之德可谓至德矣。”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乐毅走赵,赵王欲与之图燕。乐毅伏而垂泣,对曰:“臣事昭王,犹事大王;臣若获戾,放在他国,没世然后已,不忍谋赵之徒隶,况燕后嗣乎!”胡亥之杀蒙恬也,恬曰:“自吾先人及至子孙,积信于秦三世矣;今臣将兵三十余万,其势足以背叛,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,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”孤每读此二人书,未尝不怆然流涕也。孤祖、父以至孤身,皆当亲重之任,可谓见信者矣,以及子桓兄弟,过于三世矣。
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,常以语妻妾,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谓之言:“顾我万年之后,汝曹皆当出嫁,欲令传道我心,使他人皆知之。”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,见周公有《金縢》之书以自明,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,以还执事,归就武平侯国,实不可也。何者?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。既为子孙计,又己败则国家倾危,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,此所不得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为侯,固辞不受,今更欲受之,非欲复以为荣,欲以为外援,为万安计。
孤闻介推之避晋封,申胥之逃楚赏,未尝不舍书而叹,有以自省也。奉国威灵,仗钺征伐,推弱以克强,处小而禽大。意之所图,动无违事,心之所虑,何向不济,遂荡平天下,不辱主命。可谓天助汉室,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县,食户三万,何德堪之!江湖未静,不可让位;至于邑土,可得而辞。今上还阳夏、柘、苦三县户二万,但食武平万户,且以分损谤议,少减孤之责也。
看斜阳一缕,刚送得,片帆归。正岸绕孤城,波回野渡,月暗闲堤。依稀是谁相忆?但轻魂如梦逐烟飞。赢得双双泪眼,从教涴尽罗衣。
江南几日又天涯,谁与寄相思?怅夜夜霜花,空林开遍,也只侬知。安排十分秋色,便芳菲总是别离时。惟有醉将醽醁,任他柔橹轻移。
傍江亭,穷杳霭,踞_岩。水深石冷,闻道别有洞中天。待倩灵妃调曲,唤起冯夷短舞,从此问群仙。云海渺无际,波涌缓移船。
 谭元春
谭元春 曹操
曹操 张可久
张可久 乔吉
乔吉 葛立方
葛立方 文天祥
文天祥 董士锡
董士锡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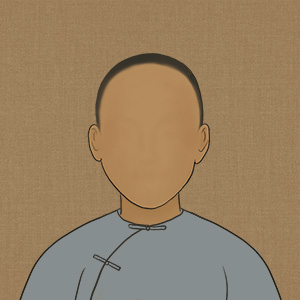 王质
王质 王炎
王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