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赏析
译文
大雅那样具有规讽意义的诗歌不见已久,如今我也已衰老,此意向谁陈说呢?
想当初,春秋战国的年代,斯文扫地,文明弃于荆榛与蔓草之中。
诸侯互相吞并,直到强秦统一六国之时,龙争虎斗,血雨腥风。
雅正之声微弱,只有屈原行吟洞庭湖边,形影憔悴,悲愤欲焚。
汉朝的扬雄与司马相如虽然文章中兴,开荡诗文的源流。
然而政治体制已然改变,政风已经沦落,难有好的诗风。
特别是汉末建安时代以来,诗歌已经走上了绮丽浮华的套路,不足为珍贵了。
如今圣上要恢复圣古时期尧舜所提倡的清净无为而治,真是天下之大幸福啊。
众多才华之士人现在遇到了清明的君主,正是风云际会,大展宏图之时。
他们正直的品格与粲然的才华交相辉映,就像天上的星星烁烁闪亮。
我的志向就是要如孔子一样,用春秋笔法,除邪扶正,让正义辉映千秋。
希望能像前代圣贤一样完成这一使命,不到获麟那样不合适的时候决不停笔。
注释
大雅:《诗经》之一部分。此代指《诗经》。作:兴。吾衰:《论语·述而》:“子曰:甚矣,吾衰也。”陈:《礼记·王制》:“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。”
⑵王风:《诗经·王风》,此亦代指《诗经》。委蔓草:埋没无闻。此与上句“久不作”意同。多荆榛:形容形势混乱。龙虎:指战国群雄。啖食:吞食,此指吞并。兵戈:战争。逮:直到。
正声:雅正的诗风。骚人:指屈原。
扬马:指汉代文学家扬雄、司马相如。
宪章:本指典章制度,此指诗歌创作的法度、规范。沦:消亡。
建安:东汉末献帝的年号(196~219),当时文坛作家有三曹、七子等。绮丽:词采华美。
圣代:此指唐代。元古:上古,远古。垂衣:《易·系辞下》 :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” 意谓无为而治。清真:朴素自然,与绮丽相对。
“群才”句:文人们正逢休明盛世。属:适逢。跃鳞:比喻施展才能。
“文质”句:意谓词采与内容相得益彰。秋旻:秋天的天空。
删述:《尚书序》:“先君孔子……删《诗》为三百篇,约史记而修《春秋》,赞《易》道以黜《八索》,述职方以除《九丘》。”
希圣:希望达到圣人的境界。获麟:《春秋·哀公十四年》:“西狩获麟,孔子曰‘吾道穷矣’。”传说孔子修订《春秋》,至此搁笔不复述作。因为他认为骐麟出非其时而被猎获,不是好兆。以上四句意谓:李白欲追步孔子,有所述作,以期后垂名不朽。
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,原作者已无法考证。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,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赏析
宋朝程颢曾把《论语》的文章比做玉,《孟子》的文章比做水晶,认为前者温润,而后者明锐。一般说来,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,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,节奏和缓,真正做到了“大雅”的风度。
开首二句“大雅久不作,吾衰竟谁陈”,是全诗的纲领,第一句统摄“王风委蔓草”到“绮丽不足珍”,第二句统摄“圣代复元古”到最后“绝笔于获麟”。这样开门见山,分写两扇,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。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,可是感慨无穷。这里的“大雅”并不是指诗经中的《大雅》,而是泛指雅正之声。雅声久矣不起,这是正面的意思,是一层。然则谁能兴起呢?“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?”落出“吾”字,表出诗人的抱负,这是第二层。可是诗人这时候,已非少壮,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“甚矣吾衰也,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”,即使能施展抱负,也已来日无多了,这是第三层。何况茫茫天壤,知我者谁?这一腔抱负,究竟向谁展示、呈献呢?这是第四层。这四层转折,一层深一层,一唱三叹,感慨苍凉,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,不露郁勃牢骚,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。
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,第三句起,就抒写“大雅久不作”了。春秋而后,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,到了战国,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。三家分晋,七雄争强,虎斗龙争直到狂秦。四句一路顺叙下来,托出首句的“久”字,但如再顺叙下去,文气就未免平衍了,所以“正声何微茫”一句,用顿宕的问叹,转一口气。“正声”即是“大雅”,“何微茫”即是“久不作”,一面回应上文,一面反跌下句的”哀怨起骚人”。《诗经》本有“哀而不伤,怨而不怒”的说法,这里把屈原宋玉,归之于哀怨,言外之意,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。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,论时代在秦以前,这里逆插一句,作为补叙,文势不平。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,“扬马激颓波,开流荡无垠”,说明扬雄、司马相如,继楚辞之后,在文风颓靡之中,激起中流,可是流弊所及,正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中所说:“竞为侈靡闳衍之辞,没其风喻之义”,和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篇》所说“扬马沿波而得奇”一样,荡而不返,开出无边的末流。诗人写到这里,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。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,“废兴虽万变,宪章亦已沦”,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,但文章法度,总已沦丧。尤其“自从建安来”,三曹七子之后,更是“绮丽不足珍”,这与《文心雕龙·明诗篇》所说:“晋世群才,稍入轻绮”,“采缛于正始,力柔于建安”,大意相近。诗人反对绮丽侈靡,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。诗写到这里,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,去古不可谓不远,写足了“大雅久不作”句中的“久”字,于是掉转笔来,发挥“吾衰竟谁陈”了。
“圣代复元古,垂衣贵清真,群才属休明,乘运共跃鳞,文质相炳焕,众星罗秋旻”,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,诗人故弄狡狯,其实半是假话。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,未尝有所谓“复元古”。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,高宗、中、睿之间,历经武后、韦后之变,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。王、杨、卢、骆、沈、宋的诗,虽各有胜处,但用“清真”两字,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,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。文才处休明之世,乘时运而飞跃,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,繁星罗布于秋天。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,比较真实,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,文胜于质,也未尝有所谓“文质相炳焕”。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,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,李白应该早就复兴“大雅”,重振“正声”,也不至于“吾衰竟谁陈”了。这六句与“吾衰竟谁陈”之间的矛盾,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,故意地正反相形的。所以下文从“众星”中跃出“吾”来,用孔子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的话,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,只有把“废兴万变”之中的那些作品,像孔子删诗一般,把它整理一下,去芜存菁罢了,这样庶几还可以“垂辉映千春”。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,赞周易、删诗书、定礼乐之外,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《春秋》,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。诗人的抱负,亦正是如此。最后两句,从“吾衰竟谁陈”,“我志在删述”的较消沉的想法,又一跃而起,以“希圣如有立,绝笔于获麟”的斩截之辞,来反振全诗,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,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。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,自比孔子,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。这一“立”字又遥遥与起句的“作”字呼应,气足神完,于是乎“大雅”又“作”了。
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,所以诗人在写作时,其胸襟风度,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,不能骏发飘逸,也不能郁勃牢骚,完全用中锋正笔。因此,即使在“吾衰竟谁陈”的慨叹之中,对当代有所不满,而只能以“圣代复元古”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,来微露矛盾之意,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,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。千古以来,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,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,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。
全诗一韵到底,音节安雅中和。最后两句,由于立意的坚决,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,“立”、“绝”、“笔”三个入声字,凑巧排列在一起,无意中声意相配,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。
参考资料:
创作背景
《古风》组诗共五十九首,此篇原列第一首。该组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,但内容大体不出“指言时事”、“感伤己遭”(胡震亨《李诗通》)两大方面。 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,说法不一。一说作于天宝安史之乱以前,所据“吾衰”一语。一说“当属早期‘大言’之作”。
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,原作者已无法考证。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,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李白(701年-762年) ,字太白,号青莲居士,又号“谪仙人”,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,被后人誉为“诗仙”,与杜甫并称为“李杜”,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“小李杜”区别,杜甫与李白又合称“大李杜”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,李白为兴圣皇帝(凉武昭王李暠)九世孙,与李唐诸王同宗。其人爽朗大方,爱饮酒作诗,喜交友。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,有《李太白集》传世,诗作中多为醉时写就,代表作有《望庐山瀑布》《行路难》《蜀道难》《将进酒》《明堂赋》《早发白帝城》等多首。
得杨八书,知足下遇火灾,家无余储。仆始闻而骇,中而疑,终乃大喜。盖将吊而更以贺也。道远言略,犹未能究知其状,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,乃吾所以尤贺者也。
足下勤奉养,乐朝夕,惟恬安无事是望也。今乃有焚炀赫烈之虞,以震骇左右,而脂膏滫瀡之具,或以不给,吾是以始而骇也。凡人之言皆曰,盈虚倚伏,去来之不可常。或将大有为也,乃始厄困震悸,于是有水火之孽,有群小之愠。劳苦变动,而后能光明,古之人皆然。斯道辽阔诞漫,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,是故中而疑也。
以足下读古人书,为文章,善小学,其为多能若是,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,以取显贵者,盖无他焉。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,士之好廉名者,皆畏忌,不敢道足下之善,独自得之心,蓄之衔忍,而不能出诸口。以公道之难明,而世之多嫌也。一出口,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。仆自贞元十五年,见足下之文章,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。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,非特负足下也。及为御史尚书郎,自以幸为天子近臣,得奋其舌,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。然时称道于行列,犹有顾视而窃笑者。仆良恨修己之不亮,素誉之不立,而为世嫌之所加,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。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,凡众之疑虑,举为灰埃。黔其庐,赭其垣,以示其无有。而足下之才能,乃可以显白而不污,其实出矣。是祝融、回禄之相吾子也。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,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。宥而彰之,使夫蓄于心者,咸得开其喙;发策决科者,授子而不栗。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,其可得乎?于兹吾有望于子,是以终乃大喜也。
古者列国有灾,同位者皆相吊。许不吊灾,君子恶之。今吾之所陈若是,有以异乎古,故将吊而更以贺也。颜、曾之养,其为乐也大矣,又何阙焉?
足下前章要仆文章古书,极不忘,候得数十篇乃并往耳。吴二十一武陵来,言足下为《醉赋》及《对问》,大善,可寄一本。仆近亦好作文,与在京城时颇异,思与足下辈言之,桎梏甚固,未可得也。因人南来,致书访死生。不悉。宗元白。
述夫帝车南指,遁七曜於中阶;华盖西临,藏五?於太甲。虽复星辰荡越,三元之轨躅可寻;雷雨沸腾,六气之经纶有序。然则抚铜浑而观变化,则万象之动不足多也;握瑶镜而临事业,则万机之凑不足大也。故知功有所服,龟龙不能谢鳞介之尊;器有所归,江汉不能窃朝宗之柄。是以朱阳登而九有照,紫泉清而万物睹。粤若皇灵草昧,风骊受河洛之图;帝象权舆,?凤锡乾坤之瑞。高辛尧舜氏没,大夏殷周氏作,达其变遂成天下之文,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。衣冠度律。随鼎器而重光;玉帛讴歌,反宗而大备。洎乎三川失御,九服蒙尘。俎豆丧而王泽竭,钟鼓衰而颂声寝。召陵高会,诸侯轻汉水之威;践土同盟,天子窘河阳之召。三微制度,乘战道而横流;千载英华,与王风而扫地。大业不可以终丧,彝伦不可以遂绝。由是山河联兆,素王开受命之符;天地氤氲,元圣举乘时之策。兴九围之废典,振六合之颓纲。有道存焉,斯文备矣。
夫子姓孔氏,讳邱,字仲尼,鲁国邹人也。帝天乙之灵苗,宋微子之洪绪。自元禽翦夏,俘宝玉於南巢;白马朝周,载旌旗於北面。五迁神器,琮璜高列帝之荣;三命雄图,钟鼎冠承家之礼。商邱诞睿,下属於防山;泗水载灵,遥驰於汶上。礼乐由其委输,人仪所以来苏,排祸乱而构乾元,扫荒屯而树真宰,圣人之大业也。
若乃承百王之丕运,总千圣之殊姿。人灵昭有作之期,岳渎降非常之表。珠衡玉斗,徵象纬於天经;虎踞龙蹲,集风?於地纪。亦犹三阶瞰月,恒星知太紫之宫;八柱冲霄,群岭辨中黄之宅,圣人之至象也。
若乃顺时而动,用晦而明。纡圣哲於常师,混波流於下问。太阳亭午,收爝火於丹衡;沧浪浮天,控涓涔於翠渚。西周捧袂,仙公留紫气之书;东海抠衣,郯子叙青?之秩。接舆非圣,询去就於狂歌;童子何知?屈炎凉於诡问,圣人之降迹也。
若乃参神揆训,录道和倪。辱太白於中都,绊乘黄於下邑。湛无为之迹而众务同并,驰不言之化而群方取则。虽复霓旌羽旆,齐人张夹谷之威;八佾三雍,桓氏逼公宫之制。洎乎历阶而进,宣武备而斩徘优;推义而行,肃刑书而诛正卯。用能使四方知罪,争归旧好之田;三家变色,愿执陪臣之礼,圣人之成务也。
若乃乘机动用,历聘栖遑;神经幽显,志大宇宙。东西南北,推心於暴乱之朝;恭俭温良,授手於危亡之国。道之将行也命,道之将废也命。归齐去鲁,发浩叹於衰周;厄宋围陈,奏悲歌於下蔡,圣人之救时也。
若乃筐篚六艺,笙簧五典。折旋洙泗之间,探赜唐虞之际。三千弟子,攀睿化而升堂;七十门人,奉洪规而入室。从周定礼,宪章知损益之源;反鲁裁诗,雅颂得弦歌之旨。备物而存道,下学而上达。援神叙教,降赤制於南宫;运斗陈经,动元符於北洛,圣人之立教也。
若乃观象设教,法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;穷神知化,应万一千二百五十策五十有五。成变化而行鬼神,观阴阳而倚天地。以鼓天下之动,以定天下之疑。索众妙於重元,纂群微於太素,圣人之赞易也。
若乃灵襟不测,睿视无涯。石昭集隼之庭,土缶验贲羊之井。稽山南望,识皓骨於封禺;蠡泽东浮,考丹萍於梦渚。麟图鉴远,金编题佐汉之符;凤德钩深,玉策筮亡秦之兆,圣人之观化也。
时义远矣,能事毕矣。然後拂衣方外,脱屣人间,奠楹兴夕梦之灾,负杖起晨歌之迹。挠虹梁於大厦,物莫能宗;摧日观於鲁邱。吾将安仰?明均两曜,不能迁代谢之期;序合四时,不能革盈虚之数。适来夫子时也,适去夫子顺也。为而不有,用九五而长驱;成而勿居,抚?霓而高视,圣人之应化也。
自四教远而微言绝,十哲丧而大义乖。九师争大易之门,五传列春秋之辐;六体分於楚晋,四始派於齐韩。淹中之妙键不追,稷下之高风代起。百家腾跃,攀户牖而同归;万匹驱驰,仰陶钧而其贯。犹使丝簧金石,长悬阙里之堂;荆棘蓬蒿,不入昌平之墓,圣人之遗风也。
导扬十圣,光被六虚,乘素履而保安贞,垂黄裳而获元吉。故能贵而无位,履端於太极之初;高而无名,布政於皇王之首。千秋所不能易,百代所不能移,万乘资以兴衰,四海由其轻重。虽复质文交映,瞻礻龠祀而长存;金火递迁,奉琴书而罔绝。盖《易》曰:「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」又云:「圣人以神道设教,而万物服焉。」岂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?
国家袭宇宙之淳精,据明灵之宝位。高祖武皇帝以黄旗问罪,杖金策以劳华夷;太宗文皇帝以朱翟承天,穆玉衡而正区宇。皇上宣祖宗之累洽,奉文武之重光,稽历数而坐明堂,陈礼容而谒太庙。八神齐飨,停旒太史之宫;六辩同和,驻跸华胥之野。文物隐地,声名动天,乐繁九俗,礼盛三古。冠带混并之所,书轨八?;闾阎兼匝之乡,烟火四极。竭河追日,夸父力尽於楹间;越海陵山,竖亥涂穷於庑下。薰腴广被,景贶潜周。乾象著而常文清,坤灵滋而众宝用。溢金膏於紫洞,雨露均华;栖玉烛於元都,风雷顺轨。丹?翠菌,藻绘轩庭;凤彩龙姿,激扬池?。殊徵?,不召而自至;茂祉昭彰,无幽而不洽。虽复帝臣南面,降衢室而无为;岱畎东临,陟名山而有事。灵命不可以辞也,大典不可以推也。由是六戎宵警,横紫殿而?金;五校晨驱,蹴元?而喷玉。星罗海运,岳镇川氵亭。登碧?单而会神祗,御元坛而礼天地。金箱玉册,益睿算於无疆;玳检银绳,著灵机於不竭。
功既成矣,道既贞矣。历先王之旧国,怀列圣之遗尘。翔赤骥而下?亭,吟翠虬而望邹鲁。泗滨休驾,杳疑汾水之阳;尼岫凝銮,暂似峒山之典。乃下诏曰:「可追赠太师。」托盐梅於异代,鼎路生光;寄舟楫於同时,泉涂改照。咸亨元年,又下诏曰:「宣尼有纵自天,体膺上哲,合两仪之简易,为亿载之师表。顾唯寝庙,义在钦崇。如闻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,并向来未造,生徒无肄业之所,先师阙奠祭之仪,久致飘零,深非敬本。宜令诸州县官司,速加营葺。」
成都县学庙堂者,大唐龙朔三年乡人之所建也。尔其州分化鸟,境属蹲鸱。萦锦室於中区,托铜梁於古地。玉轮斜界,神龙蟠沮泽之?;石镜遥临,宝马蹀禺山之影。天帝会昌之国,上照乾维;英灵秀出之乡,傍清地络。庠序由其纠合,缨弁所以会同。文翁之景化不渝,智士之风猷自远。於是双川旧老,攀帝奖而翘心;三蜀名儒,想成均而变色。探周规於旧宅,询汉制於新都。开基於四会之躔,授矩於三农之隙。土阶无级,就击壤於新欢;茅茨不翦,易层巢於故事。庄坛文杏,即架椽栾;夹谷幽兰,爰疏户牖。仪形莞尔,似闻沂水之歌;列侍り如,若奉农山之对。缁帷晓辟,横绀带於西河;绛帐宵悬,聚青衿於北海。虽秋礼冬诗之化,已洽於齐人;而宣风观俗之规,实归於上宰。
银青光禄大夫谯国公讳崇义,大武皇帝之支孙,河间大王之长子。高秋九月,振玉於唐邱;宝算千龄,跃璇蚪於太渚。我国家灵命,东朝抗裘冕之尊;宗子维城,南面袭轩裳之重。析元元之允绪,拥朱虚之禄位,拜玉节於秦京,辉金章於蜀郡。元机应物,潜消水怪之灾;丹笔申冤,俯绝山精之讼。魏文侯之拥?,道在而谦尊;董相国之垂帷,风行而俗易。
司马宇文公讳纯,河南洛阳人也。皇根帝绪,列五鼎於三朝;青琐丹梯,跨千寻於十纪。仲举澄清之辔,未极夷涂;士元卿相之材,先登上佐。冰壶精鉴,遥清玉垒之郊;霜镜悬明,下映金城之域。
县令柳公讳明,宇太易,河东人也。梁岳之英,长河之灵。沐?汉之精粹,荷天衢之元亨;旌旗赫奕於中古。组陆离於下叶。凤岩抽律,擢层秀於龙门;骊穴腾姿,吐荣光於贝阙。自朱丝就列,光膺令宰之荣;墨绶驰芬,高践郎官之右。仙凫旦举,影入铜章;乳翟朝飞,声含玉轸。临邛客位,自高文雅之庭;彭泽宾门,犹主壶觞之境。旷怀足以御物,长策足以服人。重泉之惠训大行,单父之讴谣遂远。犹为夏弦春诵,俗化之枢机。西序东胶,政刑之根本。上朝宪,下奉藩维。爰搜复庙之仪,载阐重?阎之制。三门四表,焕矣惟新;上哲师宗,肃焉如在。将使圆冠方领,再行邹鲁之风;锐气英声,一变ク渝之俗。於是侍郎幽思,ゼ凤藻於环林;丞相高材,排龙姿於璧沼。遗荣处士,开帘诠孝悌之机;颂德贤臣,持节听中和之乐。其为政也可久,其为志也可大。方当变化台极,仪刑万宇,岂徒偃仰听事,风教一同而已哉?
勃幼乏逸才,少有奇志。虚舟独泛,乘学海之波澜;直辔高驱,践词场之阃阈。观质文之否泰众矣,考圣贤之去就多矣。自生人以来,未有如夫子者也。嗟乎!今古代绝,江湖路远。恨不亲承妙旨,摄齐於游夏之间;躬奉德音,攘袂於天人之际。抚声名而永悼,瞻栋宇而长怀。呜呼哀哉!敢为铭曰:
五帝既没,三王不归。天地震动,阴阳乱飞。山崩海竭,月缺星围。礼乐无主,宗遂微。(其一)
大哉神圣,与时回薄。应运而生,继天而作。龙跃浩荡,鹏飞寥廓。奄有人宗,遂荒天爵。(其二)
尼山降彩,泗滨腾气。志匡六合,神经万类。夹谷登庸,中都历试。睿情贯一,元猷绝四。(其三)
栖遑教迹,寂寞河图。违齐出宋,历楚辞吴。风衰俗坏,礼去朝芜。麟书已卷,凤德终孤。(其四)
杳杳灵命,茫茫天秩。吾道难行,斯文易失。式宣六艺,裁成四术。虚往实归,外堂内室。(其五)
邈矣能仁,悠哉化主。力制群辟,权倾终古。陆离彩粲,蝉联茅土。涉海轻河,登山小鲁。(其六)
皇家载造,神风四极。检玉题祥,绳金署德。聿怀圣迹,同享天则。乃眷台庭,爰升衮职。(其七)
玉津同派,金堤茂版。智士高风,文翁泽远。淳壤沃,声和俗愿。载启仁祠,遂光儒苑。(其八)
沈沈壶奥,肃肃扃除。灵仪若在,列配如初。槐新市密,杏古坛疏。楹疑置奠,壁似藏书。(其九)
泛泛寰中,悠悠天下。徇名则众,知音盖寡。?石参琼,迷风乱雅。仲尼既没,夫何为者。(其十)
水欲新而釜欲洁,火恶陈而薪恶劳。
九蒸暴而日燥,百上下而汤鏖。
尝项上之一脔,嚼霜前之两螯;
烂樱珠之煎蜜,滃杏酪之蒸糕;
蛤半熟而含酒,蟹微生而带糟。
盖聚物之夭美,以养吾之老饕。
婉彼姬姜,颜如李桃,
弹湘妃之玉瑟,鼓帝子之云璈,
命仙人之萼绿华,舞古曲之郁轮袍。
引南海之玻黎,酌凉州之葡萄,
愿先生之耆寿,分余沥与两髦。
候红潮于玉颊,敬暖响于檀槽,
忽累珠之妙唱,抽独茧之长缲;
闵手倦而少休,疑吻燥而当膏。
倒一缸之雪乳,列百柂之琼艘。
各眼滟于秋水,咸骨醉于春醪。
美人告去已而云散,先生方兀然而禅逃。
响松风于蟹眼,浮雪花于兔毫。
先生一笑而起,渺海阔而天高。
 李白
李白 白居易
白居易 柳宗元
柳宗元 王勃
王勃 苏轼
苏轼 张鎡
张鎡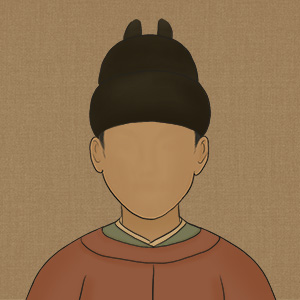 顾夐
顾夐 欧阳炯
欧阳炯 刘克庄
刘克庄 萨都剌
萨都剌